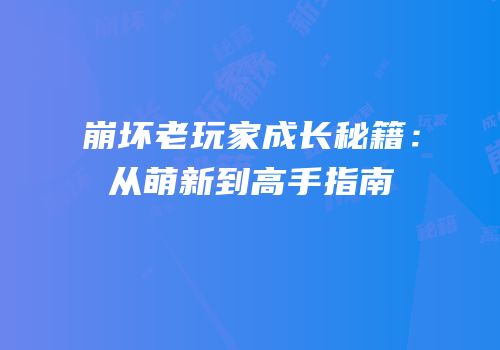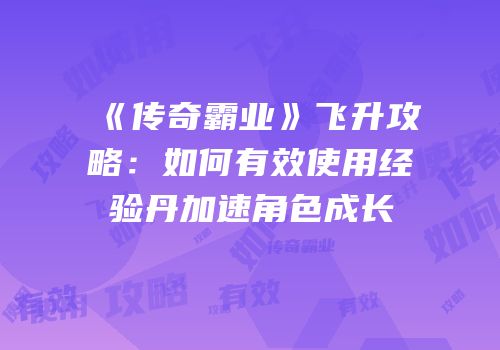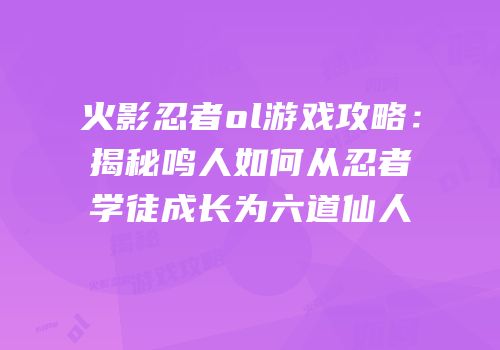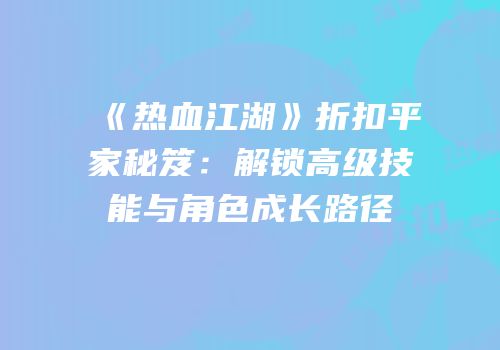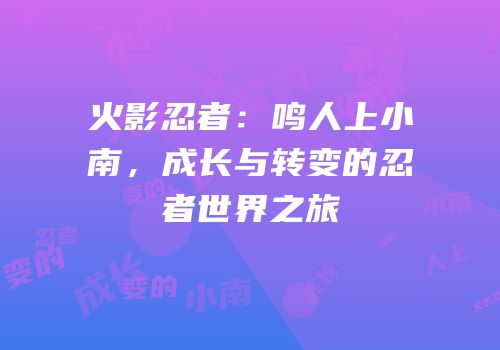教室后排的座位总是被阳光晒得发烫,但我的心里却像被冰封过一样冷。那是我转学后的第三周,因为浓重的乡音和数学试卷上刺眼的红叉,我成了同学眼中“格格不入”的存在。直到陈老师推开那扇教室门,我才尝到了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滋味——像初春融化的山泉,清冽却温柔。
第一次见她时,她抱着一摞作业本,灰白的头发随意扎着,眼镜滑到鼻尖,却对着全班笑得像窗外的海棠花。“我叫陈秋萍,你们的新班主任,”她顿了顿,目光扫过缩在角落的我,“也是你们的校园妈妈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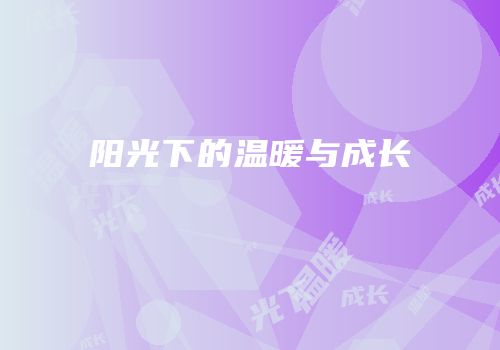
那个称呼在两周后变得具体。期中考试前的暴雨天,我蹲在走廊尽头哭得发抖——弄丢的复习资料、被雨水泡烂的作业,还有嘲笑我“结巴”的声音,都像石头压在心口。忽然有双磨出茧子的手握住我的手腕,陈老师羽绒服上的樟脑味混着体温罩下来:“来,老师口袋里有糖。”
她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成了我的秘密基地。每天午休,她会把批改到一半的作文摊在桌面,给我腾出半张椅子。当我磕磕绊绊读课文时,她织毛衣的竹针会规律地敲着桌沿,像在给我的方言打节拍;当我终于写出完整的二元一次方程解法,她突然从蓝布包里掏出个铝饭盒,里层结着冰碴的杨梅汁酸甜沁人:“这是奖励勇敢小孩的。”
毕业那天,她往我书包里塞了本《汪曾祺散文集》,扉页上有行小楷:“善良的滋味,是允许别人笨拙地生长。”现在每当我翻开书页,恍惚还能闻到杨梅汁的清香,听见竹针敲击木桌的笃笃声。那种味道永远温热,那是老师用手心捂热了岁月里所有酸涩的时光。